



| 数字场馆 (123) |
《新淤地》是由河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河口区文化馆编撰出版的文学艺术期刊。自创刊以来,立足河口,面向全市,辐射全国,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拥有一大批高层次作者和忠实的读者群,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装帧制作,在全国县级文学艺术杂志中堪称翘楚,得到了广泛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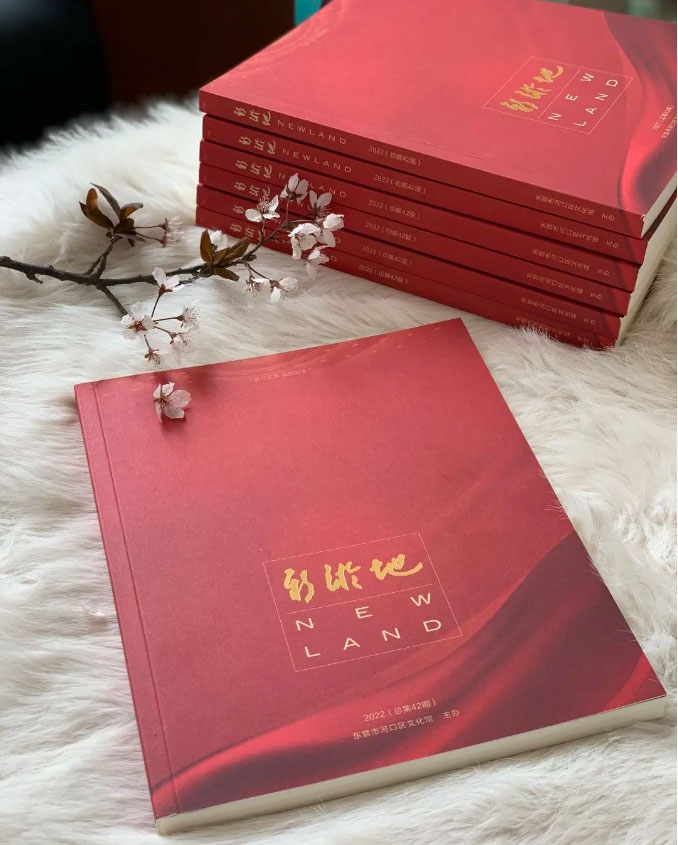
《新淤地》第42期内容包括庆贺二十大,踏上新征程、散文·随笔、诗歌、古韵新声、小说、评论六部分,从多个层面贴近读者需求。为让读者全面了解《新淤地》,展示我区文艺人才风采,河口区文化馆将对《新淤地》作品进行展播。本期请欣赏:张君亭《散文短章(四题)》
《散文短章(四题)》
张君亭
草芽儿一样的童年
大概是五岁或者六岁,应该不错,因为我那时还没有上学,我是六岁开始上学的。
就是那年仲春季节,一天的半上午,我和小伙伴们在大街上玩耍,德平和高发自豪地向我炫耀,他们各自从他们爷爷那里要了两毛钱,要到公社的供销社去买糖块儿,邀我一起去,那是极度贫穷的岁月,两毛钱、糖块儿都是奢侈的,我很羡慕,我看见我奶奶正坐在街头的碾盘上晒太阳,就跑过去缠着跟她要钱,奶奶不放心地问:你们三个小孩能去得了供销社?德平说他去过好几回了。奶奶从她大襟衣服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卷儿打开,奶奶没有找到两毛的纸币,只好找出一张五毛的递给我,我不要,我非要跟德平和高发一样的两毛钱,奶奶说只有五毛的五毛比两毛还多,我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我还不知道数字的大小,只想要两毛钱不想要不一样的五毛的。
我们迫不及待地向着供销社飞跑,恨不得插上翅膀,虽然只有二里路,但这也是我人生初始第一次没有大人带领独自离开村庄。
到了供销社,虽然很小的门面在我们眼里简直成了十里洋场,又像进了博览馆,我们三个从这头走到那头又从那头走到这头,看不尽的“十样景”观不完的“万花筒”。
靠街的一扇窗子外边装着活动的木板没有卸下,与里边的玻璃形成镜面效应,玻璃上映着清晰的图像,我们当时以为是另一个房间,可是奇怪,怎么没有门呢?我们反复跑到外边查看,外边只有墙壁啊!研究了半天到最后也没研究明白。
我们沿着柜台来回地看着从未见过的货品,肥皂的香味樟脑的香味水果的香味甜点的香味,香极了!货架上方还挂着一溜画着广告画的大木板画,卖水果的柜台上方有一幅画满了鲜艳的水果图案,有香蕉苹果梨橘子,还画着一个切开的西瓜,绿皮红瓤黑籽儿,似乎正等着人来饱餐呢,看得我们直流口水!
买糖的时候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德平和高发拿了两毛钱就打算买两毛钱的糖——很简单,可是我拿了五毛钱怎样才能买两毛钱的糖呢?这个问题太复杂了,我暗自埋怨我的奶奶太没有办法,竟然连一张两毛的钱都没有。问问卖货的女售货员:五毛钱能不能买两毛钱的糖?她说能买,还得找钱,“找钱”——这又是怎么回事?问题更复杂了,我们三个到一边商量怎样帮我用五毛钱买两毛钱的糖,我提出用我的五毛钱换他们的一张两毛钱,他俩都坚决不肯,我好说歹说德平才跟我换了。
我们买了糖往回走,我觉得有点不对劲,怎么德平用五毛钱买了两毛钱的糖还又得到一毛钱和两毛钱?我就跟他要,开始他不同意,我们三个坐下又开始商量,商量了好半天,高发也觉得德平应该把那一毛钱和两毛钱还给我,最后德平痛痛快快地把钱还给了我,这时我们三个才弄明白原来我的五毛钱是最多的,我们三个更高兴了——我们终于解决了一个巨大的难题!
回到村里,奶奶还盘腿坐在街头的碾盘上,远远地看见我们就大声呼唤,她应该是等急了,我们跑到奶奶近前,德平说:“奶奶,你放心吧,我跟你说了我去供销社都好几回了。”奶奶张着没了牙齿的嘴巴笑呵呵地说:“你给我丢了宝儿我可用拐棍打烂你的屁股。”我怕德平不高兴,小声安慰他:“别理我奶奶,她可厉害了,连我爸爸都怕他。”
村里晌午的炊烟飘起来,德平和高发各自回家了,我把剩下的糖块儿和钱递给奶奶,奶奶剥了一块糖送进嘴里,把另外的糖块儿给我装进兜里,把剩回的三毛钱又放进她那个布包卷儿,奶奶拄着拐棍儿牵着我的手走回家去。
家乡春日亭午暖阳下的的炊烟真香啊!
俗话说“日月穿梭催人老,人过青春没少年”,每当回忆起那一天的情景,就像回到了阳光灿烂草芽儿初发气息慵慵的春日故乡,就像又回到了纯真懵懂像糖块儿一样甜的童年时代。
此时夜深,灯光下,我饮一口茶吸一口烟,找一张五毛的人民币拿在手里,好像是奶奶刚刚给我的。
当年的糖块儿哪儿去了?
熏鸭子
我十岁,一九七五年冬天的一个傍晚,外面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这重要吗?似乎并不重要。
天早早暗下来,母亲烧火做饭,灶火红彤彤的,屋里很暖和,点着一盏小煤油灯,闪着昏黄的光芒,有点像糖的颜色,我就着灯光痴迷的读一本《雁翎队的故事》的书。是借村西头韩龙的,好多同学借他都不借给。我与韩龙已四十二年没见面了,很想念他!
我上三年级,韩龙上五年级,他很调皮也很聪明,喜欢和我玩,后来他成为我们村第一个从学校里考出去的大学生。我本来有希望继他之后成为第二个大学生,我的命运出了意外。
《雁翎队的故事》是一本系列短篇小说集,讲的是冀中平原上白洋淀一支叫雁翎队的抗日武装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
父亲坐在饭桌一边,他唤我准备吃饭,我已经痴迷,哪里理会,唤了五六次,声调高且严厉起来,我才恋恋不舍坐到饭桌的另一边,父亲拍着他旁边的一个小板凳:“坐这里,跟我坐一块儿。”其实,我愿意和母亲坐在一起,但父亲从那些日子开始往后,再不让我和母亲并坐,硬让我和他一起坐,似乎坐他旁边的位置有被看重的意思,母亲独坐一边显得有些落寞,母亲有时看着我和父亲笑,笑得我莫名其妙。
母亲一打开锅盖热气腾地弥漫房顶,屋里更暖和了,在热气下面我看看父亲,看看被热气围着的母亲,感觉真有趣。两大碗一小碗地瓜粥端上桌,父亲和母亲每人一大碗,我一小碗,饭桌中间放一碗熬白菜一碗蒸咸鱼,这在当时贫穷的农村已经是不错的饭食。我问父亲:
“爸爸,熏鸭子好吃吗?”
《雁翎队的故事》里数次提到熏鸭子。注意是熏鸭子而不是熏鸭,别小看这一字之别,不信请你试着分别读读,读熏鸭子的时候,舌下保证有口水流出来。当然,也许是我的错觉。
“应该好吃吧,爸爸也没吃过。”
“书里说好吃,比油条好吃吗?”
“傻孩子,油条怎么能比得上呢。”
嚿,比油条还好吃,那得有多好吃!
“爸爸,等我长大了一定上白洋淀买三只熏鸭子,咱们每人一只,不,买四只我和妈妈每人一只你两只!”
《雁翎队的故事》书中的故事情节自然吸引我,但多次对肥嘟嘟熏野鸭子的描写更让我垂涎欲滴。
“爸爸,白洋淀在哪里?”
“白洋淀?不知道。”
父亲把我的头向他怀里揽了揽轻轻地抚摩着。他肯定被童年的我的一句空头支票感动得一塌糊涂!
是的,如果我的儿子对我这样说,我也会高兴的,但我的儿子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那个夜晚,马戈庄村一百六十几户人家,再没有人知道,远方一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食物正激起一个十岁孩子的馋欲,这种食物从此深深地镌刻在他稚嫩的心灵上。
父母去世了,我长大了。熏野鸭子至今一次未曾吃过,以后也不可能吃得到,因为野鸭已属野生保护动物。熏鸡经常吃到,我想从熏鸡里吃出熏鸭子的味道,终不如意;到长江一带吃白斩鸭,既不是熏制的,也不是白洋淀的野鸭子。
我始终难以忘怀童年时垂涎的白洋淀熏鸭子,几十年过去了,有时恍惚觉得似乎曾经吃过,定心一想,确实没有吃过。
二零一三年,我从网上邮购了一本原版的《雁翎队的故事》,翻找出几处对熏鸭子的描写,没错,一点没错,久违的熏鸭子穿过四十年的岁月又来到我的眼前。
我不由地向着它来的方向走去,走去------
我当年对父亲的承诺,如何才能实现呢?
玉米羹
早晨与妻散步,走得较远,路过一处偏僻的玉米地,时已深秋,下过清霜,田野一片肃杀,玉米早被农人收获,只剩下秸秆站立着,都已死亡干枯,在地边竟发现了两株依然翠绿的玉米,还结了两个硕大的玉米穗,剥开看看,籽粒饱满鲜嫩,和妻子掰了拿回家。
在这个季节里,多么难得。
我让妻子把玉米用擦床擦成颗粒,做了一小盆玉米羹。
刚喝了一小口,就像醉了一样,口舍不得往下咽胃像伸出贪婪的手。说甘似甜,说甜像甘;浓香里饱含着鲜美,鲜美里透着浓香。
猛然,却又是很自然地想起了故乡,想起了童年,想起了去世已三十七年的母亲。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喝母亲做的玉米羹。
每年的金秋八月,新玉米成熟了,生产队把收获的玉米穗分给各家,总有少量未及成熟的玉米穗,在那粮食几乎数着粒吃的贫穷岁月,这样的嫩玉米穗谁家也不愿意要,母亲却不吱声,她知道她的儿子喜欢喝玉米羹呢。
放学回到家,母亲笑着迎我,堂屋的饭桌上放一碗香气扑鼻的玉米羹,感觉屋外的阳光都格外灿烂。
童年时喝玉米羹,只是感性地喜欢,玉米羹真正的味道,既不能准确感知又不能用语言表达。
要说我在家乡短暂的童年里,吃过什么美味,母亲做的鲜玉米羹,即是其一。
我的童年,物质生活多么贫瘠,但家庭氛围又是多么幸福,父亲晃着宽阔的臂膀,像大山一样扛着风雨,我则沐浴在母亲无边的母爱里。
父母早早地离开人世,我们一家三口人,只剩下我自己,流落异乡,而今,两棵偶遇的玉米让我意外享受了奢侈的温情。
这两颗玉米,莫不是我的父亲母亲幻化而成?
著名作家洪烛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南方的鱼》,说到在江苏南通吃河豚鱼、吃河豚鱼皮时,说了这样一番话:“我审视眼前河豚的皮(已被厨师事先剥下,搁在鱼背上),确实布满粗硬的毛刺,刚刚放到唇边,顿觉如砂纸或猪鬃般扎人。主人笑了,教我将鱼皮放回盘中,翻过来卷着吃,即毛刺冲内而背面光滑软组织冲外(跟穿翻毛皮袄似的),以避免正面的细刺戳口。他建议最好整个吞下,不要咀嚼。又说这样消化后,极其养胃,鱼皮融化成稠浓的汁液,会给胃壁覆盖上一层起保护作用的黏膜。我试着这么做了,感觉良好,胃里顿时暖融融的。像一只肉乎乎的小手在胃里按摩。”
我把洪烛先生的文章讲给妻子听,我说:洪烛先生吃河豚鱼皮的感觉像是专为我今天写的,她笑道:“你喝玉米羹还能喝出河豚的美味!”我说:“我不曾吃过河豚鱼,但我想,只怕洪烛先生的河豚倒未必能比得上我的玉米羹。”
咸 菜
现在,到好一点的饭店吃饭,如果点菜是包桌的话,饭店大多会先配送几盘小咸菜,装咸菜的盘很小,咸菜数量也不多,正菜上来之后,就会把这些小盘压到下面,小盘里的咸菜一般无人问津,它们更多的只是一种点缀而已,可是我却对它们情有独钟,许多朋友看我吃这些小咸菜津津有味,觉着奇怪,他们不知道我的心思,这些小咸菜虽然是咸的,但我却能品出其中甜的味道。
我小的时候,农村还极为贫穷,哪里有油炒菜吃?所以,家家户户必得腌上一缸咸菜,这一缸咸菜,是各家各户一笔重要的物产。当然也有有缸而无咸菜的,因为主人买不起咸盐,甚至,极个别更为贫穷的人家连咸菜缸也没有,所以当时经常有吝啬之人乘到邻居家串门偷人家的咸菜疙瘩。我母亲常常为自己能打理得一家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不缺咸菜吃而自足。我小时候,因为特殊原因,我家在短短几年内搬了两次家,母亲都是先把咸菜捞出来,把咸菜水仔细地舀出移到别处,等把咸菜缸搬到新住处后,再把咸菜、咸菜水担过去放进缸内,可见一缸咸菜水是多么珍贵。
粗饭咸菜伴着我从小到大进了中学。在中学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习极为紧张,学校里规定,不管远近,只准同学们在星期天的傍晚,赶回家去拿下一星期的干粮咸菜,并且当天晚上必须返回学校,一个星期只能拿这一次。因此,星期一二的时候,大部分同学都会有改善的好一点的咸菜,星期二三,咸菜还尚能无虞,到了最后一两天,可就惨了,咸菜大都绝尽,干粮已经干馊,实在难以下咽,这时如能寻到谁的一点咸菜,真是喜出望外,可是,难哪!独有一个叫刘西勋的同学,就是星期天中午这最后一顿饭,他也吃得十分自在,不慌不忙,安详地坐在自己的位上,喝一口白开水啃一口干粮,好像吃得还很有滋味,后来,终于有一个同学发现了他的秘密,原来秘密就在那碗白开水,刘西勋的家里很穷,他每个星期只从家里带很少一点咸菜,然后,在书包里包上一小包盐粒,没有咸菜的时候他就喝着淡盐水啃干粮。刘西勋现在在平度市医务部门任主治医师。
一九八四年正月里,一位朋友请我们几个人到他家里吃饭,去时,已准备得十分丰盛,开席前,他看着一桌的好菜佳肴,感慨地问我们:“你们知道我们家一九六一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吗?”我们摇头,他让我们猜一猜,试着猜了几种情形,他都摇头,最后他给我们讲述了他们一家那一年过年的情景:
那时,他们一家八口人,有奶奶、父母、三个哥哥、一个妹妹,他那一年五岁。大年三十这一天晚上,一家人围着饭桌坐着,坐着干什么呢?坐着就是坐着,饭桌上一无它物,锅里是空的,灶是冷的——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奶奶和父母直叹气,许久许久之后,忽然母亲走了出去,回来时,进门就喊:“孩子他爹,快生火!”这位朋友姊妹几个扑到母亲身边一看,母亲的手里抓着几块黝黑黝黑的咸菜疙瘩,原来他家咸菜缸的水里竟然还有几块漏网的咸菜!他父亲把锅里添上大半锅水,生起火来,屋里霎时有了暖意,他母亲将几块咸菜细细地切碎,煮了大半锅咸菜汤,他清楚地记得:他和妹妹、奶奶碗里的咸菜块比哥哥们的多点儿!
他们一家,之前吃的是什么?之后又是如何度过的?我没有问这位朋友,因为他的眼眶已经湿润了。
二零零五年初冬,我跟另一位朋友到他老家,给他的父母送过冬取暖的煤炭。从他父母家往回走时,朋友刚发动起汽车,我从后视镜里看到他年迈的母亲从院子里追出来,手里端着一个小盆,我示意朋友不要启车,他的母亲走到车窗跟前对他说:“捎点儿咸菜回去吃吧,这是今年刚腌的,你从小爱吃。”朋友看了看,说没法带,便执意拒绝了母亲。车渐渐离了他家门前,他苍老的母亲端着一盆咸菜还站在那里。我以为,这位朋友是粗心了,他或许没有意识到,孱弱的母亲已不能再走向田间地头,挥动健壮有力的臂膊,再给她的儿女们创造什么财富了,但是,连咸菜都惦记着自己儿女的这样一位母亲,她还有什么不在惦记着她的儿女?!这让我这个旁观者好生羡慕——我从小失去父母,我多么希望在寒风里站在大门前,落寞地端着一盆咸菜的这位老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呀!
现在,超市里的咸菜颜色鲜丽,价格不菲。妻和邻居们腌咸菜,经常一起探讨切磋,已经不仅仅是放上咸盐完事,还要加入料酒、白糖、果片、调料、香油、味精等等,其配方复杂得如我难以尽述。这样的咸菜于我却没有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