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数字场馆 (123) |
《新淤地》是由河口区文化和旅游局主办,河口区文化馆编撰出版的文学艺术期刊。自创刊以来,立足河口,面向全市,辐射全国,发表了大量优秀文学艺术作品,拥有一大批高层次作者和忠实的读者群,无论是内容质量还是装帧制作,在全国县级文学艺术杂志中堪称翘楚,得到了广泛赞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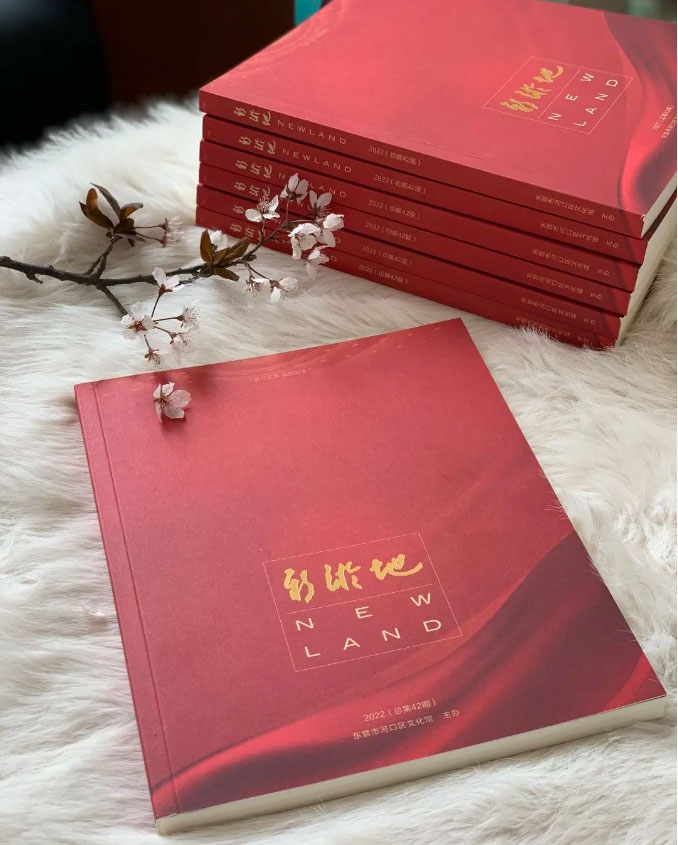
《新淤地》第42期内容包括庆贺二十大,踏上新征程、散文·随笔、诗歌、古韵新声、小说、评论六部分,从多个层面贴近读者需求。为让读者全面了解《新淤地》,展示我区文艺人才风采,河口区文化馆将对《新淤地》作品进行展播。本期请欣赏:鲁北《从前慢》
从前慢
鲁 北
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
这是木心先生创作的一首诗歌,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里。2011年底,木心先生去世,《从前慢》开始被人传颂,甚至被当成了情诗,在各种社交平台广为流传。诗人概括了普通百姓最普遍的感受,即对于快节奏下慢生活的向往,尤其是这慢里透着的人性朴素、浪漫、耐性、果决,而且是让人看得懂却深觉文学的魅力。诗中用从前的慢节奏与一个愈来愈快的对世界的感受相比,转化成了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
乡村是宁静的,我在宁静的乡村里,度过了一段宁静的时光。
——题记
我种地的那些年
有生产队的那会儿,我还上学,假期里也干农活,那不叫种地。
所谓种地,就是从耕种到收获,自己亲力亲为。
我结婚之后,没有分家。等到弟弟也结了婚,父母把我和弟弟分了出去。
说是分家,只是从一个锅里摸勺子,分成了三个锅里吃饭。种地的事,还是大家伙儿齐下手。虽不同时收割,但同时播种。那时候,不多的几亩地,相邻不远,或地边搭着地边,或隔着几户人家。往往是,播种了,父亲招呼一下,一起把种子播到地下。是种豆子、种玉米、种棉花,还是种麦子,各自做主。
那些年,什么时候种什么庄稼,我不知道,全听父亲的。我只跟随着,干点力气活。
管理是自己的事,施肥是自己的事,收割是自己的事。
春上,把玉米种子埋进地里,过不了多久,嫩绿的玉米芽钻出了地面,顶着晶莹的露珠。被风一吹,柔软的身姿像柳条,千姿百态。
要间苗了。我握着锄,把多余的苗挖去,留下粗壮的那棵。
要锄草了。我握紧锄把,把锄扔出去,再拖回来,锄去野草,也翻松土地。
要施肥了。我把大把大把的化肥,撒到玉米不远的根系处,让这些根系慢慢地吸收。我似乎听到了玉米拔节的声音。
接着,玉米长到一人高了,结玉米棒棒了。
这个时候,我会掰几个鲜嫩的下来,拿回家里,煮煮吃,一家人尝尝鲜。
过不了多久,玉米粒饱满了,一排排鼓胀胀的。
把成熟的玉米棒棒掰下来,运到家里。竖起梯子,一点点摊放到房顶上。房顶上一片金黄。
父亲在村西的地里锄黄豆,弟弟在村西的地里锄高粱,我在村西的地里锄棉花,我们离得不远。一阵阵的风,吹着庄稼,也吹着我们。
太阳西下,倦鸟已归。父亲锄完最后一锄,直起腰,看了看远处。他扛起锄,走到附近的弟弟的地里,俯下身子,和弟弟一起锄起来。几垄地,用不了多时,锄完了。父亲扛起锄,走在前面,弟弟跟着后面,来到了我的地边。不一会儿。我们爷仨,把我剩下的那片地锄完,一起回了家。
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在一起劳动的。
麦熟一晌。割小麦是庄稼人一年中最累的农活,“过一个麦季,脱一层皮”。头天晚上,家家户户“磨镰霍霍”,用磨刀石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第二天天不亮,麦地里就已经人头攒动。太阳才刚刚露头,一片一片的小麦,已经被割倒了。
村子北边的不远处,是我们的一个场院,父亲已经早早地把它压实,打扫干净,等着小麦们来这里安家。
每年割麦,我们都是集中收割,谁家的成熟了,先割谁家的。弟弟开着拖拉机,一趟趟把小麦运到场院里。母亲负责翻晒小麦,负责烧水做饭。
收割结束了。选一个晴朗的天,把麦子摊在场院上,开始打场。
一家一户的麦子并不多。往往是,我们三家的麦子摊在一起,中间放的薄一些,作为分界线,在一起打场。起场以后,父亲拿起扫帚,扒拉成三份,谁也不说什么。
秋天打豆场,也是这样。
父亲说,什么你的、我的、他的,都是我们的。
我们一直这样,很多年。
直到我离开老家,去县城工作,我不种地了。父母年龄大了,也不种地了。剩下的地,由弟弟耕种。
其实,那些年,我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种过地,只是干了一些农活。
作木匠
作木匠,在我们鲁北地区,是指那些没有经历过科班学习的木匠,属自学成才,是半路出家,也叫半拉子木匠,或半木匠。
我父亲就是一个作木匠。
1974年,我父亲33岁,他决定在自己的老宅子上盖五间新房子,三明间,一里间,一单间。原来居住的那三间低矮的房子,被风刮过,被雨淋过,被日晒过,房顶时常漏雨,墙皮不断脱落,已经不能再遮风避雨了。
盖房子需要木匠。
木匠的活儿,不少。铺地基线了,拾掇梁檩了,做椽子了,装屋梢了,按门窗了,等等,都是。
没有木匠,盖房子,叫空谈。
但附近的三五两庄里,没有木匠。
父亲托亲戚、找朋友,四处打听。
好不容易,在二十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打听到一个。
父亲把他请了来。盖房子的事,拉开了序幕。
这位木匠,木工活道尚可,但无匠心,好酒又好茶,很难伺候。茶水凉了不行,酒烫了不中。
对此,父亲有微词,但敢怒不敢言。物以稀为贵。盖房子离了人家,不行,转转不动。
那些天,父亲忍气吞声,直到房子盖到一定的高度,上上梁,排好檩条,父亲的心,才舒展了。
那时,父亲暗暗发誓,要学做木工活儿,为乡亲们出一点力。
房子盖好不久,父亲就买来斧子、锯、刨子、锛、凿等木工工具,空闲时,用自己的废木料,三锛两凿的实践起来。
第二年,父亲在自己的院子里盖了两间偏房,没请木匠。自己琢磨着,该锯的锯,该锛的锛,该刨的刨,该凿的凿,鼓捣了三五天,把梁、檩、椽、梢等,都拾掇好了。
渐渐的,父亲成了远近闻名的作木匠。之后,街里街坊们有盖房子的,他就去给人家拾掇房檩。耳朵上夹一支铅笔,又锯又锛、又凿又刨的,干木匠干的那些活儿。
父亲有盖房子的经历,知道里面的艰辛。因此,街里街坊有盖房子的,无论自己的农活多忙,家里的事情多急,他都是有请必到,甚至不请自到。
那时候叫帮忙。谁家盖房子了,娶媳妇了,嫁闺女了,老了人了,乡亲们都会放下自己手中的活儿,去帮忙。在乡下,一代一代的庄稼人,就是这样,相互帮衬着,过日子。
父亲给人家做木工活儿,尽心尽力。有时候,为了赶活儿,才在人家家里吃一顿午饭。往往是,放下碗筷,顾不得喝口水,就忙碌起来。
后来,父亲学会了做椅子、做桌子、做板凳、做柜子等简单的家具。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下人大都一贫如洗。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无奈,也有凳子断了榫,桌子三根腿,门窗开了缝的尴尬。
农闲时、下雨天,邻居们拿着断了榫的凳子,三根腿的桌子,找我父亲,帮着修理。
也有做新家具的。父亲大多把木料拿到家里来,偷忙待闲,给人家做起来。那年代,没有电锯,我放了学,不去割草、剜菜的时候,就和父亲拉锯,锯木头。父亲站着,弓着腰,拉上锯。我坐在地上,垫上一块毯子,拉下锯。拉下锯不容易,虽然木头上画着墨线,也仍然会拉偏了,常常被父亲纠正。拉锯时,木头沫子纷纷扬扬,随着风,刮进我的眼睛里,钻进我的鼻空里,灌进我的耳朵里。
我常常抢着干这干那。有时候,把锯好的木头,放在宽宽的凳子上,一头顶在凳子的那头,我骑在上面,或用麻绳勒着这头,在下面用脚蹬紧,用刨子把木头刨平。刨起的木片像海里翻卷的浪花,木头的清香,沁人心脾。有时候,我在锯好的没有上凿卯,在父亲画好的地方,放上凿子,用斧头敲打着,一凿一凿的凿下去,直到符合标准。我的一举一动,俨然一个小木匠。
那时候,父亲年轻,帮着人家盖房子、做家具,很多年。
不经意间,父亲上了岁数,就不干这种营生了。
那些木工工具,渐渐的,也不知道去了哪儿。
如今,仅存的几件木工工具,挂在西屋墙上的一个角落里,诉说着那段历史。
逮 鱼
我喜欢逮鱼,我弟弟也喜欢。喜欢逮鱼,是男孩子的天性。
童年的记忆里,我的家乡雨水很多,河河沟沟也很多。那个时候,一遇到连雨天,河沟、水渠里的水,就溢到陆地上,一些鱼,也跟随着,游过来。停了雨,没多久,那些水会倒流到河沟里、水渠里。但低洼处的水是流不回去的。那里的鱼,也游不回去。那低洼处的水,便成了鱼们的暂时栖身地。
我几乎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是去湾里挑水。从家门口到村南的那个湾,有三四百米的弯弯小路,要经过一片小小的芦苇地。
芦苇大都生长在有水的洼处。
这些芦苇,不是《诗经》里那些芦苇,但有《诗经》里那些芦苇一样的情怀。“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夏季里,雨水充沛,芦苇“随风而荡,却止于其根,若飘若止,若有若无。思绪无限,恍惚飘摇,而牵挂于根。”芦苇是滚滚红尘里的有情之物。
到了秋天,雨水少了,芦苇丛中的水,也渐渐少了。只有更低处,有七零八落的水洼,在太阳的照耀下,闪着微光。清风吹过,水面上有些许的涟漪。
那一日,我挑水路过,听到有水鸭子在芦苇丛中“嘎嘎”乱叫,我停下脚步,放下扁担,向芦苇丛中走去。远远地看见,在一小块水洼里,一些鱼在翻越,那一湾水,已经装不下鱼们游来游去的梦。原来这里有不小的水面,渐渐地,小了,更小了,最后成了锅盖那么大的一片。鱼们游不动了。
我拿过来挑水的水桶,不费吹灰之力,把那些鱼逮进水桶里。
村子的四周有许多的河沟,虽然不大,但终年有水。还有一些低洼处,终年也有水。有水则有鱼。我们七大八小的孩子们,结伴去逮鱼。
逮鱼分攉鱼、戗鱼、摸鱼、撒网,等等。我们多是攉鱼、戗鱼、摸鱼。
有一种很专业的工具,叫“戗网子”,形状看起来像一个用渔网打底的簸箕,有长长的柄。使用的时候,贴着水下的泥皮向前冲,在某个瞬间迅速抬起来,水和泥漏下去,鱼和草留下来。
这是对付小鱼最好的工具。
对于我们逮鱼,父亲有微词,但也没有呵斥。他总认为,庄稼人要本分,要好好的侍弄庄稼。父亲常说,“逮鱼摸虾,耽误了庄稼。”
童年时光,一触即逝。少年岁月,也匆匆而过。到了十七八岁,我就很少逮鱼了。
弟弟还逮鱼。但他已经不是攉鱼、戗鱼、摸鱼了,而是撒网逮鱼。
村西边有一条沾利沟,有一条永新河,下游都连着渤海。潮涨潮落,经常有鱼逆流而上,游到沾利沟里、永新河里。农闲时,弟弟就拿上渔网,去打鱼。有时候,晌午时光,也去抡两网。
河沟里盛产梭鱼,弟弟每次都收获五六斤、十来斤,甚至更多。
母亲会把这些鱼拾掇干净。父亲把拾掇干净的这些鱼,放到油锅里,炸好,放到盘子里。
我周末回家,都能吃到鲜美的梭鱼。
父母知道我喜欢吃这种鱼。每每弟弟打了鱼,都炸好了,放在冰箱里,等着我周末回家吃。临走的时候,再给我捎上一些。
我知道,父母也喜欢吃这种鱼,弟弟也喜欢。但他们总是说,有空再去打。
他们种庄稼,哪里有那么多的空啊,我知道。
攉 鱼
攉鱼是一项很累的营生,但我不嫌累。俗话说,鲜鱼头上三尺火,极是。
天上下雨,坑里有水;坑里有水,水中有鱼。
我喜欢攉鱼。
我小的时候,村里的土地宽满,但大都是撂荒地,可以耕种的农田并不多。撂荒地不长庄稼,只长野草。
我家门前不远处,有一片洼地,几乎一年四季有水。村子的大西北,有一片洼地,足足上千亩,四周是茂盛的芦苇,洼地里长满苲草。赤足蹚在水里,看到有鱼儿在游弋,不等你靠近,它箭一样去了远方。
有时候,我到门前的洼地里,或村外的芦苇边,摸鱼、捕鱼。更多的时候,是攉鱼。
村西有一条河沟,河沟两岸是一畦畦的小菜园。有葱、蒜、韭菜、茄子、辣椒,等等,绿绿葱葱的。
夏季里,雨水充沛,河沟里积存很多的水。这些水,似乎是一些死水,直到秋后,甚至还晚,才渐渐干涸。
这条河沟在我们村境内,有三四公里长。沟帮上长满野草,野草里常常有一些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飞起来,飞向天空,飞到远方。
我经常在这条河沟里攉鱼。
星期天、节假日,这条不再流动的河沟,是我的乐园。
在去攉鱼之前,我已经无数次站在沟帮上,观察水里的动静,以此来确定那一段水域里,鱼比较多。
攉鱼有技巧。水很深的时候,不能攉鱼。那样会费很多的力气,才能把水攉干净。
我已经在这条河沟上,观察了七八天,眼看着水位在下降。“七月八月地如筛,九月十月水上来。”眼下正值八月,是水下降最快的季节。
待到河沟里水面缩短到三四米宽,水深降到三四十公分的时候,我扛着铁锨,提着水桶,雄赳赳、气昂昂地来攉鱼了。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把沟帮上的土,一锨锨挖起来,找准与对岸垂直的距离,一锨锨垒起来,直达对岸。
一条水坝,建成了。
然后再向前或向后五六十米,垒一个水坝。
这样,就有了一块固定的区域。
在这个固定的区域里,再进行分割。分割成五段或六段。
接下来,用水桶把两个水坝之间的水,一桶一桶地攉水。
弯下腰,打水;直起腰,把水泼出去。往返上千次,上万次,已是精疲力尽。
水越来越少,力气也越来越小。
猛一抬头,看到水位下去了百分之八十。已经能够看到有鱼在游动。
我顿时来了精神,又弯下腰,一桶一桶地攉起来。
这时,我身上沾满了污泥,粗布裤衩,成了污泥的颜色。站在水里,裸露的躯体是极易变色的,我黝黑的皮肤变得更加黝黑,我的脸上、身上都是污泥,我活脱脱一个泥猴。
水已经很浅了,一些鱼露出了背鳍。稍微大一点的鱼,只能偏着身子,在浅水里游来游去。
水净鱼清。鱼已经不能在水里藏起自己,只能贴着沟底的污泥,扑扑愣愣。
我弯着腰,把鱼一条一条抓进水桶里。
接着,再攉邻着的那个池子里的水。
这次要轻松一些。先在岸边开一个小口,让水位高的池子里的水,自流到刚刚攉净的那个池子里。然后把口子堵实,开始攉将起来。
一个池子接着一个池子的,攉干净,把鱼都逮起来。
天渐渐黑下来。
趁着没人,我脱下裤衩,在清水里涮涮,拧两把,穿在身上,把水桶别在锨把上,一转身扛在肩上,哼着小调,向家的方向,走去。
一晃四五十年过去了,我已经找不到我以前攉鱼的那些地方的影子了。
湾
“拖拉机,进了庄,不是老蒋,是老康”,这句顺口溜,在我们小村流传了很久。
老蒋何许人也?蒋广礼是也。老康何许人也?康寿宝是也。一个是油田管子公司的司机,开拖拉机的。一个是油田管子公司的工农员,也不知道啥官。村里人都习惯称呼他俩一个蒋师傅、一个康师傅。
我们村西南角的那个湾,就是蒋师傅用推土机挖出来的。
我们那里跟水库,叫湾。
1960年代末,村北来了钻井队,村子里热闹起来。
接着,村子附近建起了许多厂房,大批油田后勤单位安营扎寨在那里。
油田要在村子附近钻井,找石油,需要和村里打交道。村子的四周长满庄稼,一片连着一片,绿油油的。老百姓好端端的庄稼,不能说糟蹋就糟蹋了。油田是国有企业,不会那么做,他们要给适当的赔偿。于是乎,油田和地方就得搞工农关系。
这老蒋和老康,就是来村里搞工农关系的。
据我父亲讲,那时候,村里种的地瓜、花生、西瓜,常常送到管子公司去,分给职工和家属们。管子公司的汽车、拖拉机,也常常给村里运输庄稼。
我们小村人口不多,但居住分散。小村南北宽不足一里,东西长却三里有余。村里有一个湾,在村子的东北角,我们住在西北角,去挑一担水,来回六七里,一个早上也就能挑两担水。村子西南角有一个湾,但很小,雨季里存一点水,到了秋天,就渗光了,还是得去村东北角的湾里挑水,费时费力。
那一年,老蒋开着推土机,没白没黑的干了半个多月,把西南角的那个小湾,挖大了好几倍。
从此以后,一湾水,可以供居住在村子西边的村民们,吃一年,几乎不用去村东北角的湾里挑水了。
多少年来,我们都是喝湾里的水,喝不上井水。湾边是沙土,十分松散,挖下去极易塌方,砌不成井。
湾里的水不卫生。人饮用,牲口也饮用。自觉的村民,用水桶把水提到岸上,让牲口喝,不自觉的直接把牲口牵到水边,让牲口伸长脖子,把嘴扎进水里,咕咚咕咚地喝起来。牲口没有自制力,有时候边喝边排泄,把屎和尿撒进湾里。
还有,大雨季节,湾四周的雨水也冲进湾里,夹杂着野草、禽畜粪便。
雨季里,父亲从屋檐上接一些雨水,饮用。
春上,父亲把一根三四米长的玻璃钢管,从中间锯开,开口向上,把它固定在屋檐下面,一头略高,一头略低,在略低的一端绑上一根塑料管,连接到屋檐下的瓮里,下雨时,屋顶上的水流下来,流到玻璃管里,通过塑料管,流进瓮里。父亲用这样的方式接水,许多年,直到村里通上了自来水。
冬天里,也吃雪水。把干净的雪,挖进屋里的水缸里。
村子里通上了自来水,吃水就不愁了。
忆往昔,早上去湾里挑水的人,络绎不绝,人们站在岸上,说说笑笑。那里成了小村的“井台会”,新闻发布中心。
眼下,那两个湾都废弃了,像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帆布包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我的青葱时代。那时候的年轻人,留长发,蓄胡须,带墨镜,穿喇叭裤,肩上挎一个黄色帆布包,帆布包的一侧,镶嵌着红红的“为人民服务”,一枚红五星,闪闪发光。这应该是那个年代年轻人的标配。我没有留长发,没有蓄胡须,没有带墨镜,也没有穿喇叭裤,只挎一个黄色帆布包。
我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文艺青年。
1980年,我爱上文学了,爱的一塌糊涂。天上的白云,地上的庄稼,远处的风,身边的影子,都是分行的文字。诗歌不是海市蜃楼,而是我的宗教。
一个黄色帆布包里,装着席慕容,装着汪国真,装着一支钢笔,装着几页稿纸,装着我的梦。
我无论走到那里,那个黄色帆布包就跟到那里,像我的影子,似我的情人。
她跟着我,去过济南,求师拜友;到过东营,和文友切磋诗意。她一直静静地陪伴着我,不张不扬,不离不弃。
她坚守着我多少秘密,只有我知道。
一首首诗歌,一封封信札,带着她的体温,去远方。
远方不远,也不近。漠河、拉萨、海南岛……都是。
她不嫌弃我,依偎在我身旁,像依人的小鸟,似燃烧的火焰。
我爱着她,她也爱着我。她像我,我像她。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
习近平总书记也有一个包。在《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里有这样的记述:
习近平的父亲母亲都是老干部、老党员。由于父亲习仲勋从1962年受冤屈,母亲齐心带着尚未成年的小儿子习远平在河南省黄泛区的一个农场劳动,两个姐姐被下放到生产建设兵团,习近平也前往陕北插队。
一家人天南地北、骨肉分离。妈妈的心里又怎能不挂着孩子们,怎能不挂着远在陕北农村吃苦的儿子。她便亲手给习近平缝制了一个针线包,上面绣了三个红色的字:娘的心!
在梁家河的日子,习近平没有让母亲失望。那些年,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习近平什么活儿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7年的农村生活,使他和陕北乡亲们结下了深厚情谊。1975年,习近平被推荐到清华大学读书。离开的那天,全村人排起长队为他送行,很多人不舍地哭了,不少村民送他走了一程又一程。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时,把母亲绣的针线包“娘的心”送给了邻居张卫庞以作纪念,就像他说的“我的人走了,但是我把我的心留在了这里。”
人生有些许的遗憾。
不知道哪一年,我把我的包弄丢了。
自己拼了命,也想不起来是怎么把她弄丢的。
我翻箱倒柜地找过她,去梦里寻过她。并非“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并非“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并非“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这个黄色的帆布包,是找不到了。
我不仅仅失去了一个黄色的帆布包,失去的是一个时代。
拾 粪
拾粪是一种营生。这种营生,是乡村里勤劳的人干的。
记忆里,我的三爷爷、邻居二爷爷和住在村中央的黄大娘,都是勤劳的人。天刚蒙蒙亮,我去村小学上学的路上,经常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他们也陆续作古,但现在想起来,还如在眼前。
拾粪需要工具,一是粪筐,二是粪叉子。粪筐分两种,一种是背在肩上的,我们习惯叫它粪篓子,U字形,口大底小,口处有提手,提手与底部,有绳子连着;另一种是提着或用粪叉子挑起来扛在肩上的,我们习惯叫它粪篮子,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篮子。
我们的小村坐落在黄河口岸边的荒原上。黄河口有大片的紫荆,也有大片的紫穗槐。紫穗槐和紫荆是编筐的上等材料。
我爷爷是编筐的能手。编粪筐,编土筐,也编抬筐。除了自己用之外,还拿到集市上去买。
常年拾粪的人,习惯用粪篓,背在肩上可以省力气。
生产责任制之前,生产队里养牛、养驴、养马、养骡子。生产责任制以后,家家户户养牛、养驴、养马、养骡子。都是为了犁地、拉车之用。这些牲畜,都是人的好帮手。
人,可以自律。就是多么内急,也要找个旮旯,行方便。牲畜不管那一套,它们不分场合、不分地方,拉屎、撒尿,谁拿它们也没有办法。有时候,它们驾着辕、拉着车,走着走着,冷不丁扬起尾巴,肆无忌惮地把屎拉在路上,把尿撒在地里。走路的人不高兴,拾粪的人却喜欢。
我的三爷爷是勤劳的。初冬时节,天天起大早,去拾粪。
拾粪全凭运气,有时候转悠大半天,也看不见一堆粪。
其实路上的粪并不多。
我们的小村很偏僻,四周长满庄稼和野草。屋子的近处,有庄稼,有野草。屋子的远处,有庄稼,也有野草。
我家屋子的前面是一条土路,土路的那边就是野草。大多的时候,我看见三爷爷在杂草丛中拾粪。拾的是牛粪、马粪、狗屎、或猪屎。三爷爷把这些粪拾回家,放在粪池里,沤着。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那时候没有化肥,庄稼靠的是人便、猪屎、牲口粪和土杂肥。
路过一片茂盛的庄稼地,人们指指点点,问这是谁家的庄稼,长得这么出众,熟知的人提着我三爷爷的名字说,这是李荣和家的。人们投去赞许的目光。
俗语讲,“地里上满粪,粮食堆满囤。”我的三爷爷深谙这些道理,红火的日子,从拾粪开始。
近读迟子建的长篇小说《烟火漫卷》,她在后记中写到,冬天生产队的牛马认得我,那时上学除了交学费,还得交粪肥,只要发现公家的牛马出来拉脚,我就提着粪筐尾随着。可有时你跟了半里地,它们一个粪球都不赏,我便赌气地团了雪球大牛马,这时总会遭到车老板的叱骂。
这就是那个时代,迟子建的塑胶跑道。毫无疑问,经历历练,回春后的大地一定会生机勃发,烟火依然如歌漫卷。
我上学的时候,也勤工俭学,但没有交过粪。我拾过粪,但不多。我知道,每个小村里,都有早起拾粪的人。
“有空多拾粪,没事少赶集。”我不能像三爷爷那样早早起来拾粪,但我要做一个勤奋的人,热爱生活,好好生活,种好自己人生百花园里的一棵棵庄稼。